青岛刘圣文琅琊赤子的琅琊梦
2020-04-30 09:50:36 来源: 食品安全导刊
青岛刘圣文琅琊赤子的琅琊梦
本刊记者 朱有刚
山东省青岛市刘圣文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是一位痴心不变的琅琊之子,几十年来,他对这片热土的耕耘始终没有停止。他先后向国家收集捐赠了以新石器时代为代表的石器、化石、陶器、钱币、字画、碑碣、拓片等数百件珍贵文物,他对琅琊文化的研究使得琅琊台旅游景区的开发既有了扎实的历史依据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了大量的考古佐证和文物资料。他立志同千百万琅琊赤子一道,将美好的“琅琊之梦”变为现实。

20世纪70年代初,青岛琅琊台还是一座荒山,孤寂凋敝,无人问津。在查遍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之后,这座光秃秃的山在一位生于斯、长于斯、钟情于斯的年轻人的心中撒下了梦的种子。
如今这位年轻人,如今已到了花甲之年。“琅琊台和‘挣筋山’之间有一条沟,叫跺脚沟。我第一次在那儿捡到一枚小铜镜,经鉴定,是春秋战国时的文物。正是这枚小铜镜照出了我的路。”盛开的幸福透过刘圣文的眼睛温暖了乍暖还寒的初春。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受了《西海岸周刊》的采访,这个不起眼的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一张放着文房四宝的书桌占了近半个房间的宽度,其余的地方则被各种书籍所充斥着。一切的摆设,都写满了主人的荣耀。

名人之后,“不务正业”
“我出生于琅琊湾畔的刘家村。”刘家才人辈出。明清之际,刘家五世祖刘元化中过举人,任过县令,写的一手好狂草。他的儿子刘翼明以贡生授予利津县训导职务,一生写了许多诗文,传世的有《镜庵集》等。
刘圣文“自幼受琅琊文化的熏陶”。他喜欢看书,也爱好文艺。农家清贫,没有钱买乐器,他就自己动手制作。“我用蛤蟆鱼皮代替蟒皮蒙琴筒,用牛尾代替马尾为弓毛。”一个二胡就这样诞生了。之后,他又迷上了绘画、书法。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不务正业。“我觉得工作时好好干,业余时间也要利用好。别人打扑克、侃大山,我就用来练书法、绘画。无非是选择不同。”

这种“不务正业”的作风延续到了刘圣文在文化站的工作中。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包村,一个乡镇划成几个管区,将工作触角深入到农村中去。为了在干好中心工作的同时,兼顾做好琅琊台文物的发现、搜集和保护工作,抱有“私心”的刘圣文主动请求领导安排他负责琅琊台所在的台东管区。“当时我家在离该管区10余公里的刘前村,哪个管区也比这个管区离家近。”

他靠亲戚朋友凑钱买了一辆破旧自行车,一边跑农村中心工作,一边入村入户摸底调查。“叮叮当当”的自行车交响乐回荡在沉寂的大地上,一次次叩击琅琊文化沉重的大门。然而,沉重的现实还是给满怀激情的刘圣文当头一棒。
喜讯越浓烈,遗憾越刻骨
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十分缺乏。有一次,刘圣文到一个村支书家了解情况,发现小孩在玩一个釉陶罐。刘圣文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重要的文物,于是急忙问村支书是从哪里弄来的。村支书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进行村街规划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在场的人有说这是盛骨灰的,有说是南方来北方占地用的,气不过的社员用铁锹当场拍碎了好几个。刘圣文心疼地忙把釉陶罐抱在怀里,在炕头上和村支书一条一条地讲文物保护法。
这件事让刘圣文意识到,要是以实物来宣传保护文物,效果会更好。“讲是主要的,言传更要身教。”刘圣文把从村支书家拿回来的釉陶罐细心地涮净,拴上尼龙绳,走到哪儿提到哪儿,提到哪儿讲到哪儿。“刚开始,别人看见我拿着‘盛骨灰’的罐子都说我神经不太好。”曾经被误解的苦恼已经成为刘圣文讲述这段过往时堆满眼角的笑意。
无论是管区召开各村干部会,还是村里召开社员大会,在讲完中心任务后,他便见缝插针地宣传琅琊台文物搜集、整理和保护的重要意义,讲一些具体的保护办法和注意事项。甚至上级为表彰他工作突出而颁发的奖品——电视机也被他用来宣讲保护文物。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凡是主动捐献文物和保护文物有贡献的人,他都会利用社员大会、小广播、黑板报、光荣花等形式进行表扬。

后来,“周围群众一有文物信息,就会说‘快到文化站找小刘’”。
于是,保存了三代的《琅琊刻石》拓片、《琅琊台图》、“千秋万岁”瓦当、68枚战国时期的齐刀币、青釉盘口双系釉陶壶等文物就这样陆续被捐献出来或者发现。《琅琊刻石》的发现,结束了其他市、县关于《琅琊刻石》所在地的争论,被湮没了千年的琅琊台开始重露容颜。
越来越多文物的发现并没有给刘圣文带来过多的喜悦,反而渗入血液的遗憾愈加在心中涌动。
工作干得越好,日子过得越紧巴
“我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完整的龙头碑。”
琅琊台上庙院内及周围原有72座龙头碑,解放初期已经被砸碎埋到沟里了,传说有勾践立的、胡亥立的、万历二十四年重修琅琊台时立的。每到一个村,刘圣文就向村里老人们询问。只要在沟坝地堰、水沟河边看见石头,就像铁末见了磁石,立即就被吸引过去了。看见他这种着了魔一样的状态,人们都好奇,这个人是怎么了,到处瞅什么?“我曾在沟底扒拉出来几块,拿回家放着。虽然都是残碑断石,字迹也被破坏,但是依然感到很珍贵。”
有一天,刘圣文和陈家台村的小道士肖元平又像往常一样谈起琅琊庙宇、望日亭碑的遭遇。对方无意间提到,解放初年村里打井,由于砌井台缺少条石,村里曾组织人到山顶拉过石碑。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刘圣文的警觉,他随即便前往井口查看。讲到这里,刘圣文非常兴奋,甚至当场给记者画出了井口条石的示意图,“我当时趴在井台上,把镜子伸到下面,看到了碑的下面真的有文字。”默默藏在井口几十年的颜悦道所立的《登琅琊述》石碑,就这样被刘圣文挖掘了出来,佐证了琅琊文化的丰厚和久远。“圆满了。”
由于文化工作特别是文物工作搞得比较热火,因此县上下来的人很多。当时文化站没有经费,刘圣文只能在自己家里招待,所以工作干得越好,日子过得越紧巴。“搜集到那么多文物就没想着自己留一件吗?”周刊记者追问道。“没有,我觉得文物放在博物馆里才最安全。既方便观赏,又便于研究。放在自己手中和被埋藏在地里都一样,没有价值。”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刘圣文调离了琅琊文化站,但是他的琅琊文化研究之路却没有被就此切断。除了将自己的搜集、研究成果载入了《琅琊之梦》、《琅琊台》等书籍外,他还和钟安利、张国光、王景东等提出了“琅琊文化”概念,并撰写了大量文章阐述观点,进行论证。现在,“琅琊文化”这一概念已被很多专家学者予以接受。2013年,退休之后的他又自费创办了“琅琊书画天地”网站,借助网络来代替几十年前走街串巷地宣讲琅琊文化。
从最荒凉的旅途走出最美的风景。作为未知领域的开拓者,面对的困难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下去?”
之前还滔滔不绝、声音洪亮如钟的刘圣文陷入了短暂地沉默。
“我始终坚信,琅琊台是一座会被越来越多人重视的文化宝库。”
热点推荐
-

主要食品配料厂商携手支持可持续农业
-

别样肉客在华推出脆香酥炸植物基蟹饼,为新春佳节增添美食新选
-

ADM首度亮相FBIF2023,探索食品饮料的今天、明天和未来
-

专访婴儿水团体标准制定者:为何为婴儿饮用水制定更高标准?
-

使用梅特勒-托利多X光机的五大理由
-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守护“舌尖上的年护“舌尖上的年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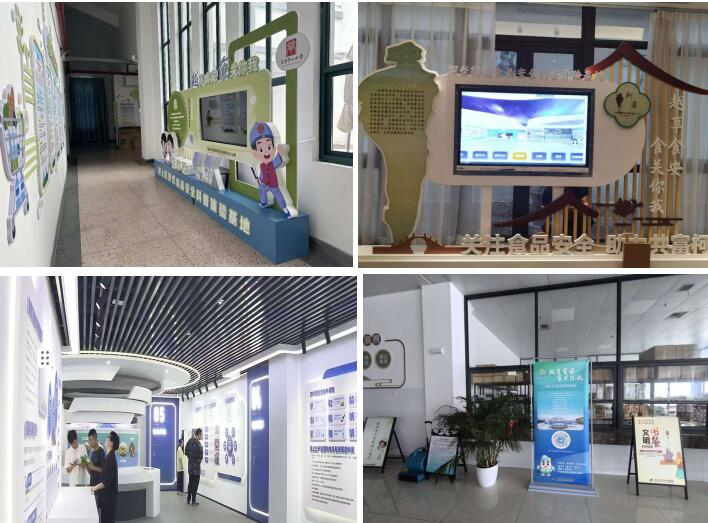
绍兴市掀起全民食品安全VR科普热潮
-

溧阳市监局天目湖分局:开展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

溧阳市监局上黄分局:开展食品小作坊安全培训
-

溧阳市监局古县分局:提升食品安全意识 共建安全健康生活
-

你在各大火锅连锁品牌吃到的蘸酱,就来自奉贤这家企业
-

庆“八一” 强党纪 常律已担当起
-

溧阳市监局社渚分局:强化行风建设,筑牢安全底线
-

强基地促高质发展,贺州西麦生态旅游工厂建成投产
-

溧阳市外卖送餐行业团工委成立
-

溧阳市监局古县分局: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

科普“童”行 仪征市市场监管局开辟校园科普“微阵地”
-

仪征市市场监管局马集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安全检查
-

南京市浦口区开展食安科普进校园活动
-

“异地注销”不用愁 “跨区通办”解民忧
-

主题党日在五月 按律规范新跨越
-

力办实事解民急 真心服务获锦旗
-

宝应县望直港镇召开预防食物中毒培训会议
-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
-

南京市浦口区召开食品安全二季度工作会议
-

宝应县氾水镇集中办理食品小摊贩备案登记证
-

仪征市市场监管局真州分局开展农贸市场电子秤专项检查
-

溧阳市监局社渚分局:守护养老服务机构“舌尖上的安全”
-

通州湾示范区召开农村食品安全工作推进会
-

扬州市2023年度一般及以上食品药品安全事故“0”发生





